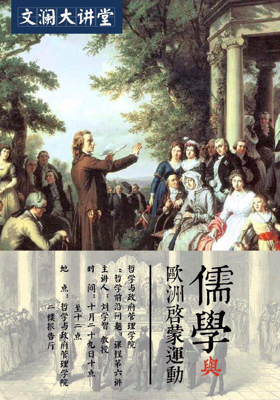
10月29日上午,文澜大讲堂“哲学前沿问题”课程由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刘学智教授主讲“儒学与欧洲启蒙运动”。刘学智老师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思考,对“复兴”一词作为纽带联系东西方,从轴心时代的思潮迸发到欧洲中世纪思想禁锢再到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的思想解放运动,分析儒学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进而说明西方文明自身的内生性与世界各地文化的发展有内在关联。
首先,刘老师以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切入点,讲述了轴心时代后,中国的文化经济日益强大,而欧洲却经历了中世纪的思想禁锢。在经历了近千年的沉睡期之后,欧洲十五世纪前后发生文艺复兴,十七到十八世纪发生了启蒙运动。刘老师对此提出了三个问题:欧洲的觉醒有没有东方因素的影响?中华文明对其形成有没有影响?西方中心主义论的观点是否存在局限?刘老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其次,刘老师从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说起,同时也引证多位国外学者的论点,指出欧洲中心主义论的局限所在,以及“必在世界整体的视野中来研究各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说明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必然是相互影响的。霍布森提出了六点理由反驳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第一,全球经济很早就被创造和维持着,到1800年,世界各主要文明一直相互联系,并有了“东方全球化”的说法;第二,当时各地区的统治者也在政策上促进全球贸易;第三,公元500年后,加强全球贸易的一套经济制度得以形成;第四,运输技术尽管不够先进,但已能够满足全球贸易的正常运行;第五,全球流动仍对许多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变革性影响;第六,“现成的传输渠道,由此使东方更加先进的资源组合传播到了西方”。从这六点可以看出,“东方全球化”开始于公元500年,此时“几乎所有隔断地区的联系都已经得到了填补”。霍布森认为,“英国的工业化明显地建立在外在性变革的基础之上,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比西方早700至2300年中国许多创造性的发明上。”虽然英国人改进了这些发明,但“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
此外,刘老师还进一步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关联。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质不是完全提倡复古,而是借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名,来宣传新的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摆脱神学统治,人性开始觉醒,理性呈现光芒,为后来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霍布森指出在激发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运动中,中国的思想格外重要。利玛窦、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学者也都对早期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往往借用孔子的名字和儒学思想来推行他们的主张。此外,包括伏尔泰在内的“许多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对理性方式的偏爱皆来自于中国”。此外,重农主义、自由精神与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对启蒙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法国大革命也深受其影响。在政治学说层面,中国的思想文化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和肯定。

最后,刘老师总结了探讨“儒学与欧洲启蒙运动”问题的当代启示。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树立自身的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启迪,同时也对如何看待西方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此外,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提倡的“五伦”,及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这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北方民族的侵略中,中华文明没有灭亡,反而北方民族被汉文化同化了?此外,在回顾历史时,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科学地理解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观,从而公正地评价世界各地区所有民族在不同时代的建树。我们也应该转换视角,尝试在西方文明中探索、反思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缺少的东西,通过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使中西方文化兼容并蓄,这是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的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